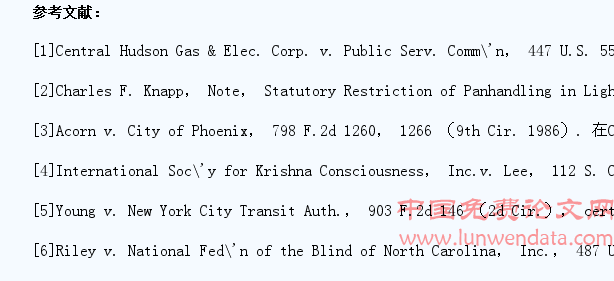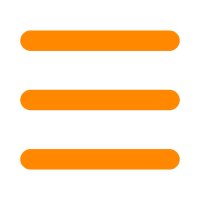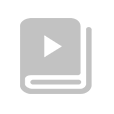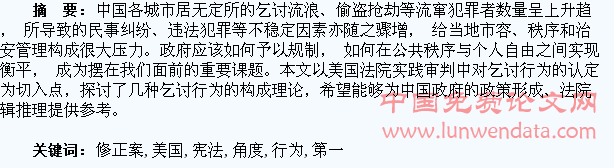
1、商业言论
虽然存在争议,但一般觉得乞讨构成商业招揽由于钱转移到乞讨者手上之后,乞讨者会依据自已的意愿来用这类钱。因此,虽然乞讨仍然可以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却要比其他受保护的言论的保护程度要低一些。也有人倡导乞讨过程中,施予者并没从乞讨者身上获得任何东西,因此乞讨并不是商业言论,应当得到第一修正案完全的保护。
在Edenfield诉Fane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注册会计师招揽顾客的禁令。法院觉得招揽顾客是一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商业表达。因此,只有当政府能证明这种规制只是为了达成重大的政府利益时才能绕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约束力。Kennedy法官讲解道“一项对个人招揽行为的禁令的合宪性在于招揽者和被招揽着的身份,与招揽当时的环境”,“某一种招揽行为,即时并不是具备欺诈性也会由于它的频率或激烈程度,使得招揽的对象感到威胁、烦恼、或骚扰。而保护公众免受此种招揽行为带来负面影响是一项合法要紧的政府利益 ”。
Fane案中,政府想要禁止注册会计师从其他会计师手中招揽顾客。法院将注册会计师招揽的对象描述为“十分知道会计师服务的商业主管”。想要获得正当的原因来管制这类会计师的招揽行为,政府需要要证明“此种管制行为是为知道决某种紧急的问题,并且政府马上施加的阻止手段确实可以非常大程度上解决此种问题。Fane 案中,政府未可以证明对会计师招揽行为的管制构成一项重大的政府利益”。根据Fane中法官的逻辑,一旦法院认定乞讨行为构成商业言论,那样只须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可以证明乞讨者会对环境导致不利影响或者给海量行人带来威胁,乞讨行为就非常或许会被限制或者禁止。
2、公共平台理论
政府对那些在长久以来被用来进行公共演讲的地方进行的言论的管制需要满足更高的需要。Black大法官和Roberts大法官曾在Hague案判决书的引导段中写道:“(公园和街道)长久以来都被觉得是公共场所,被公民用来进行集会,交流思想和讨论公共问题。”假如同意两位法官的看法,并需要政府只能依据与达成压倒性的政府利益有严密关联性的法规来管制街道上的乞讨行为,可能干预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在一项判决中指出,将街道归类为传统公共平台并不需要意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形下都永远可以进行自由言论。
乞讨行为是不是应该遭到保护,并未必要打造在公共平台理论之上。乞讨作为一种招揽行为,与在街道上集会游行或者拿着标识牌站在路边不同。尽管在ISKCON案中,最高院基于认定机场不是公共平台而支持了一项禁止在机场进行招揽的命令,但Kennedy大法官同时也承认,即便机场被认定为公共平台,这项禁令不会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他觉得“即便对于公共平台,也存在着对言论管制的规范,而依据这类标准,机场管理部门对于在其航站楼内的招揽和同意资助行为的管制应当被支持。只须言论 管制只须符合适当的时间,地址和方法,或者针对表达行为的非言论部分”在乞讨被作为一种纯言论而遭到保护的体制中,公共平台理论使得政府可以限制在某些环境下的乞讨行为,譬如地铁上。5依据公共平台理论,政府在非公共平台中对言论有关的行为的管制权力远远大于其在公共平台中的管制权力。因此,界定平台的性质十分要紧,若是非公共平台,那样政府管制乞讨的行为更有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审察。
3、慈善募捐
依据最高院的看法,慈善募集一般都与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密不可分,因此需要被视作遭到保护的言论。有人觉得这种紧密关系式是因为慈善资金的募集体现美国经济分层体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
在Village of Schaumburg诉Citizen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中,募集者用募集到的资金来进行募集演说。慈善组织应该违反了“75%的募筹资金应当用来进行捐助而不能用于机构管理”。在Schaumburg案中,最高法院觉得“募筹资助无疑受制于适当的管制,但此种管制需要十分小心,由于事实状况是,募集行为一直与为了特定目的寻求支持或者与表达对特定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的权利密不可分。”
在Young 诉 New York City Transit Authority案中,第二巡回上诉法庭将乞讨和慈善募集区别开来,并用措辞严厉地写道:“有组织的慈善基金通过增进交流和传播思想来服务社会,然而乞讨行为除去对公共利益导致威胁以外,一无是处。”然而Meskill法官在Young案中指出,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角度来看,乞讨与慈善募集并无差异。不如此觉得的话,就意味着个人的困苦在法律上来讲,比某个组织维护的利益得到更少的保护。
在Loper 诉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案中,第二巡回法院的法官觉得乞讨构成慈善募集:“频繁的乞讨一般随着着期望得到食宿,衣物,医疗保障或者交通费的言语。即使没如此的语言,一个蓬乱不堪,无家可归的人伸出手索要救济的形象本身就传达了需要帮助的信息。大家觉得为慈善组织募筹资金的人和为自己寻求救助的人之间在信息传达方面没任何差别。两者都是寻求别人的慈善救济。从宪法第一修正案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别十分微小。”
4、O'Brien标准
尽管需要资金或者同意资金资助的行为可能是行为而非表达,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行为同时也传达了一种“需要支持和帮助”的信息。如此,对乞讨行为的管制就需要从最高院在美国诉O'Brien中进步出来的规范来进行考察。依据O'Brien 标准“政府的管制的需要在宪法赋予的权力范围内推行;或者是为了达成要紧和实质性的政府利益;或者达成政府利益并不会抑制言论自由;假如对言论自由的偶然管制低于达成政府利益所需要的程度。” 但,最困难的问题是这一标准到底是不是适用。假如乞讨行为本身被认定是一种言论,那样对乞讨的管制无疑超越了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这一问题存在着非常大争议。当然也可以为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先假设乞讨时一种言论,然后继续探讨这一标准的其他原因。
在Loper案中,警署争辩道很多乞丐用不真实或欺骗的方法来骗取钱财,或者成天守在银行或者ATM机旁边,假如允许他们聚集在一块,他们无疑会变得愈加有攻击性。因此,对于乞讨行为的管制是为了控制乞讨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威胁,而这一权力完全在政府正常的管制权限之内。可以看出来,在Loper案中,警署正是企图通过说明对乞讨行为的管制符合要紧的政府利益来证明其管制的合理性。
在美国诉O'Brien中,最高院断定焚烧兵役应征卡构成犯罪,尽管焚烧行为本身作为反战示威的一部分,确实含有表达的原因。尽管政府有其他渠道来对士兵进行身份标识,但法院仍然觉得政府禁止征兵卡焚烧具备要紧的政府利益。与焚烧征兵卡的行为相比,乞讨行为就更不像是一种表达行为了。也就是说,法院应当看政府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项合法的政府利益还是为了压制言论自由来判断其行为是不是合法。如此一来,依据O'Brien案法官的建议,一旦从在适当的政府利益,只须此种利益不是微不足道的,法院就需要同意这种利益的存在,并且进一步判断O'Brien标准的最后一项内容,即“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偶然管制是不是超越达成政府利益所需要的程度”。
Loper案中,法院觉得禁止所有些乞讨明显是非必须的,由于很多不具备攻击性的乞讨并不像警署所说的那样具备风险性。假如根据文义来解析O'Brien标准的最后一项内容,那样可以非常自然的觉得,假如政府有其他的办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并且对给言论自由带来的影响更少,如此政府的行为就没满足最后一项必要性的需要。法院的解析正是根据文义来解析的。但如此的解析与O'Brien案最后的判决是不同的,由于在O'Brien案中,即便应征卡被焚毁,政府仍然是有其他渠道来标示应征者的身份的,但最高院还是支持了对应征卡焚烧行为的禁止。
在Ward v. Rock Against Racism案中,最高院认定,只须某项规定与达成政府合法切内容中立的政府利益具备严密的关联性即为符合了O'Brien标准的最后一项需要,即便这项规定并不是限制最少的办法。
法院的这一讲解给政府追求合法目的提供了空间,却没说明什么时间政府的行为可以符合O'Brien标准。同时,没对和平方法的乞讨和具备攻击性的乞讨,与非欺诈的乞讨和欺诈性的乞讨加以区份。因而法院就需要承担权衡政府一般管制和达成政府目的的责任。不幸的是,将法院放在这种地方会使得他们在审判案件的时候过多地依靠于他们对乞讨行为的个人看法。国家和地方政府禁止所有些乞讨行为由于仅仅禁止具备攻击性或者威胁性的乞讨十分困难。
O'Brien标准适用取决于法官如何权衡政府利益和乞讨对于流浪职员的重要程度。因此,尽管O'Brien案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对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却几乎没任何指导意义。
5、时间,地址和方法剖析法
在某些情形之下,“时间,地址和方法”剖析法与O'Brien标准无异。但两者又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由于限制乞讨的时间、地址和方法不会完全剥夺乞讨者表达能力。Kennedy大法官在支持ISKCON II案中的的乞讨禁令时使用了一种不一样的渠道并将禁止亲自乞讨的禁令和禁止其他方法乞讨的禁令区别开来。禁止乞讨的目的是亲自乞讨。在ISKCON II案中,他投票支持对现场索要资金的乞讨行为进行禁止,由于此种行为可能增加欺诈和胁迫的风险。同时,Kennedy大法官觉得依据管制规定,即使乞讨者没当场拿到资金,但他仍可以继续散播信息,譬如,他可以分发预先写好收件地址的信封,那些捐助者可以据此汇出他们的资助。也就是说,政府管制的内容不包含分发预先写好收件地址的信封,而是从那之后才开始。从这个角度看,如此的禁令就能被视作是一种针对特定时间、地址和方法的管制。
尽管这样,这一问题的重点仍然是是不是将乞讨行为本身视作言论。并且,预先写好收件地址的信封的替代办法是不是可行也十分值得怀疑。虽然乞讨行为当然包含当场乞讨,并且可能存在隐患,但试图通过限制乞讨的时间、地址和方法对于问题的解决也并无裨益。假如说公共街道不合适乞讨,并非出于到时间、地址和方法等原因的考虑,而是因为乞讨本身的性质。
小 结
综上可以看出,美国司法实践进步出来的各项关于乞讨行为的理论都没对于怎么样在第一修正案下保护乞讨行为提出确切的结论。这类理论多样且极具灵活性,使得法官可以选择某一种理论来支持或者反对政府对乞讨行为的管制。在这种情形下,宪法修正案是不是应当保护乞讨行为就会引发很多感性的问题,不一样的法官会依据他们我们的对乞讨者的个人喜恶来使用不一样的理论,得出不一样的法律结论。
当然,任何一种剖析都不可能完全排除私人原因。问题是,一些私人的原因或许会通过使用某种理论的伪装而被掩藏起来。因此,法院在处置某些可能包括个人感情的问题时,假如需要他们做出价值判断,那样此种价值判断应该尽可能的显而易见。依据现行的法律,法官们可以使用最高法院判例打造的多种理论来得出任何他们觉得明智的结论,并且并无需标明他们个人对于乞讨问题问题的价值取向。某一种理论假如要得到适用就至少应当使得致使结论得出的各项原因变得显而易见。